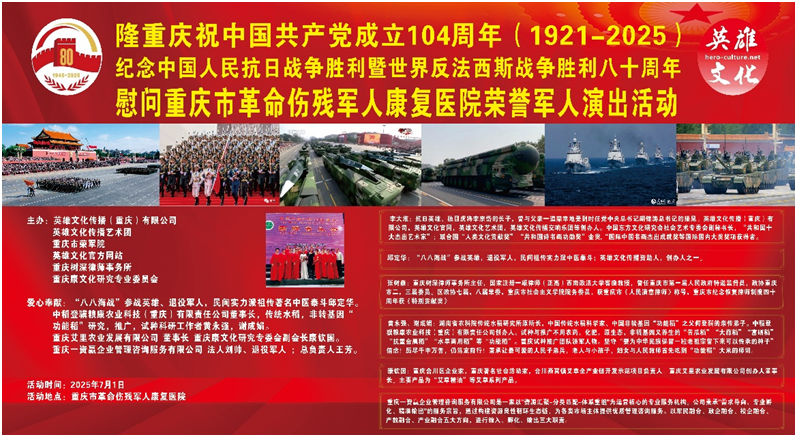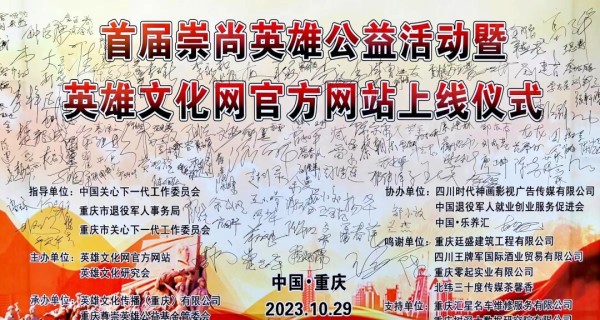编前语:原昆明军区后勤部22分部战友陈云豹(笔名乐水),应该算是当年我们战友中的大秀才了。他是上世纪1964年入伍到昆明军区军医学校,1968年毕业,先后在昆明军区139野战医院、80医院任外科军医。两次参加援老抗美筑路,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,赴老山参加全军对越轮战。参加云南通海峨山大地震抗震救灾......退休后,陈云豹还是笔耕不止,写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当年援老抗美、自卫反击作战的文章。这里转发一篇他写的《献给战争中的母亲》,分享给大家。

献给战争中的母亲
(一)
到达前线的当天,还未卸载下三天急行军的劳顿。深夜里还在熟睡就被院长叫醒,命令我带人外出抢救。卡车刚驶出岔路进入公路的主干道,只见公路的右侧停着一辆接着一辆的炮车,宛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钢铁巨龙趴在路边。车上的战士们穿着大衣,有的打着瞌睡,有惊醒了的战士拿着电筒向我们照来,好奇地想看个究竟。
寂静的公路上只有我们一辆汽车飞快地向前奔去,灯光掠过十多公里长的一辆辆炮车的车队,才到达事发地点。这条钢铁巨龙在山谷间的一座小桥边被拦腰截断,桥下的山沟里倒扣着一辆四轮朝天的炮车,火炮被甩到一边,挂钩与车体仍然紧紧相连。河沟里的水很浅,汽车和炮翻下去后,就像一道水坝拦住了涓涓细流,使水位升高。车厢里堆满了的背包等物品,把坐在大箱里的战士们紧紧地压在下面动弹不得。外面,一群战士用斧头把车厢的底板劈开,钻进去把压在里面的六个战士一一抢救出来,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活着。他们多半是被水淹死的,汽车电瓶里溢出的硫酸灼伤了他们的皮肤,一层层皮肤脱落下来惨不忍睹。
这时,一位部队首长模样的人过来询问我们谁是负责人,我赶快上前自报家门。他说,部队还要继续前进,没有办法处理这六位烈士的遗体,请我把这六位烈士的遗体拉到我们的驻地暂时停放,日后他们派人来处理。按7照惯例,医院外出抢救只负责活着的,牺牲的由部队自己处理。此时的我,清醒的意识到这是前线,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够拒绝。马上点头同意,让他们把烈士遗体抬到我们车上。
返回时,我想到大箱上躺着六位烈士遗体,这不是一般的货物,出于对烈士的尊敬,我爬上了大箱,与他们在一起,就当是他们还活着,我在护送着他们。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地沉重,刚到前线几个小时,就遇到如此惨烈的车祸,不由得一股悲壮之情在胸中激荡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谁遇到这样的情形都会悲痛万分。


在前线简易手术室抢救伤员

几天前与母亲分别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那时,我还在军区学习班学习。几个月来中越边境冲突不断,广播电视反反复复地报道着中越边境的冲突,越南的炮弹仿佛在每一位军人的母亲的心中爆炸。每天在环城路边晨练的母亲,忧心忡忡地看着一队队披戴着伪装网的战车向南开去,给她的心中增添了多少惆怅和忧虑。作为一个军人的母亲,特别是,作为一个曾经参加过两次援老抗美战争的军人的母亲,她何尝不知道这样的形势,对她那作为军人的儿子意味着什么?我也知道某一天会有一封电报命令我归队。我每天回家吃饭,明显地感觉到饭菜一天比一天丰盛,妈妈一天比一天看得多、吃的少。我低着头若无其事地大口吃饭,大口吃肉。我知道母亲一定也在看着我,也只有这样,才能够减轻她的一点焦虑,给她些许安慰。我们谁也不谈中越战事,都在貌似若无其事中等待着什么。
终于,1978年11月初的一天中午,我回到家,只见厨房里异常寂静,里屋一桌丰盛的饭菜已经摆好,妈妈静静地坐在桌前发呆,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封电报,啊!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
妈妈哆嗦着嘴唇,把电报递给我欲言又止。电报上“我部参战速归”的六个字跃入眼帘。我故作镇静地笑着对妈妈说,“明天我陪你一天,后天回去”。
下午,我回到军区招待所办理完手续,返回家中,见母亲又拿着另一封电报,在同样六个冷冰冰的字的前面多了“命令”两个字,陪妈妈一天的希望付之东流。这时候,妈妈已经意识到军情紧急,她异常平静地对我说:“老三。你就明天回去吧!”
我接过两封不同份量的电报,转身向长途汽车站奔去。凭着两封电报的“特权”,在长长的队伍中,在众目睽睽之下,买到了当年根本就不可能买到的明天的车票。此时,祖国的荣耀与安危,军人的责任与自豪跃然心头。
次日清晨,母亲牵着小侄儿送我归队。走出院门,她的眼角挂上了泪滴,走在小巷里泪如雨下,到了大街上已是泪如泉涌,一块手帕已经堵不住她那决堤的泪流。我不怕打仗,最怕见到的就是母亲伤心的泪。我想安慰妈妈,可是,浸泡在泪水里的千言万语在喉咙里涌动着,我不敢开口,只要一开口,必然是声泪俱下。小侄儿瞪着一双大眼,好奇地看着奶奶和三叔泪眼婆娑,他出奇地、静静地跟着走。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煎熬之路啊!
好不容易才走到公共汽车站。我说什么也不让母亲再送我到长途汽车站,匆匆跳上公共汽车,不敢回头直面母亲的泪眼。待汽车行走了一段路后才回过头去,透过后车窗玻璃,看见站在寒风中、佝偻着身躯的母亲还在擦拭着泪水。我完全没有想到妈妈今天是这么的伤心难过,情绪这样地反应强烈。回想起我在老挝参加援老抗美战争三年半的岁月里,不知道妈妈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,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拥被哭泣,以泪洗面。
哦!妈妈,原谅我,原谅您这不孝的儿子吧。
回到医院连夜收拾行李,第二天清晨就随医院的第一梯队出发了,一路上妈妈的泪水一直在我的心田里流淌。
今天,看着这六位烈士的遗体,不由得想到他们的母亲。而在此时,她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儿子,他们就在我的面前。在这寒风料峭的夜晚,她们是否有天人感应?她们是在安睡中,还是彻夜不眠?是在惶惶不安中,还是从噩梦中惊醒……?
我抬头仰望着黑沉沉的夜空,那无数闪烁的星光,仿佛是他们母亲那一双双无助的泪眼,在我眼前一幕幕闪过,不由得自己的眼眶也湿润起来。
我站在车厢里,身上的白大褂迎风招展,惊动了炮车上的战士们,他们纷纷探出身子,用大功率手电筒照射着我,大声地喊着问“出什么事了吗”?我无言以对。看着这一车车,一个个年纪不过20岁上下的年轻战士,他们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吗?
回到驻地,连夜料理烈士遗体。上前线时带来的五口棺材,这是还差一口。请县民政局帮忙买了一口还没有上漆的棺材,将他们全部装棺入殓。次日清晨,全体人员抬着六位烈士的灵柩为他们送葬。在一个山坡上新开辟的烈士陵园里,已经挖好的数不清的,还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墓穴静静地仰望着苍天。正在那里挖墓穴的老乡看到这样的送葬场面,也被深深的震撼了,不约而同的拿起工具,加入到送葬的队伍,和我们一道为六位烈士下葬。战友,安息吧!他们是入住这个烈士陵园的第一批园住民。
“再见吧,妈妈!再见吧,妈妈!如果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,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......”
这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后风靡全国的一首歌。母亲不喜欢它,一听到这首歌就烦躁不安,凡是有唱这首歌的地方,她就绕道而行,或者充耳不闻。她认为这是一支不吉利的歌,甚至于非常痛恨歌曲的作者和唱者,认为他们是在每一个母亲的心口上撒盐、捅刀子。
妈妈不需要山茶花,山茶花谢了,第二年还会再开放。没有了儿子,妈妈的希望也就没有了。没有了希望的人生,妈妈的生命还会那样地鲜活,那样地圆满吗?妈妈用一位纯粹母亲的情怀去评判战争,诠释她心目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,难道你不认为她也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吗?
1984年,我再一次披甲奔赴老山战场。这时的我不仅是为人儿,而且已是为人夫,为人父。当车队行驶在前线的崇山峻岭中,看着万丈深渊里的狰狞怪石,不由地想到了母亲,妻子,儿子,一阵阵的恐惧袭上心头。
临行前,我买了数十个信封,封面写好给妈妈的地址,交给爱人收好。在前线每个礼拜都同时给爱人和妈妈分别写一封信,一块寄给爱人。再由她 把信装入事先写好的给妈妈的信封里,从医院驻地寄给妈妈,。在整个参战期间妈妈都不知道我在前线。
参战结束后探亲回家,朋友来看我,问起我在前线的情况时,一旁的妈妈才反应过来。她饱含着泪水看着我一言不发。



(二)
若干年后的一天,偶遇一青年妇女,她一声“三哥”的呼唤,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。她是我家原来老邻居的女儿。她有个弟弟,姐弟俩传承了她们母亲的基因,都是高挑的个子。弟弟高大帅气、活泼可爱。姐姐亭亭玉立、楚楚动人。那时她们正读中学。每当我探亲休假,姐弟俩放学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,当看到我这一身戎装的解放军时,她们常常不知所措,不知道是叫解放军叔叔好,还是叫哥哥好,只好腼腆地莞尔一笑擦肩而过。自从我家搬出那个院子后,十多年没有见面。
今天,她见到我,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的弟弟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一天就牺牲了,那年刚满十八岁。她那大而清澈的眼眶里一泓泪水汹涌而出,亦诉亦泣地讲述着弟弟牺牲的经过。当年,她母亲虽然徐娘半老,但是风韵犹存,如今已是两鬓斑白。丧子的打击、沧桑岁月的消磨,过早地在她脸上留下了沟沟坎坎的皱纹,显得十分苍老。当说到儿子的牺牲时,她嚎啕大哭,多年干涸了的眼眶里涌出一股洪流,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没有轻重地拍打着我的手背,嘴里一声接着一声喊着:“三哥呀,小强那时候为什么没有遇到三哥你呀……”。她完全把我当做一个能够拯救她的儿子的人。
看着母女俩悲痛欲绝的样子,我久久地沉默着。这个时候,迟到的安慰已属多余。我脑海里全是那个英俊潇洒、满脸稚气的小强。仿佛看到他走在连长的后面,却倒在了连长的前面。他那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,大地为之颤抖,河水为他哭泣。他的人生永远止步在18岁,军龄3个月。
更让我痛心疾首的是,小强的部队正是我被派遣深入到前线阵地时所在的那个团。他所在的一营穿插敌后,夺取桥梁截断敌人的退路,配合主力围歼了驻守发隆的一个营的越军,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解放军报把这次战役作为我军穿插、包围、全歼敌人的典型战例,在头版位置加以长篇报道。他们团在那次战役中阵亡60多人,负伤180多人,没有想到,阵亡的60多个战友里就有小强。
第一阶段的战役结束后,我还去过那个停放遗体的树林里看过他们,为他们整容、缝合残缺的肢体和伤口。



(三)
50余年前(1968年——1974年)的那场援助老挝人民,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,是我国十数万部队援外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场秘密战争,我们称之为援老抗美战争。这是继抗美援朝战争后的又一场境外作战的援外战争。我军有210位烈士葬在老挝的两个烈士陵园里。
前年,一群老兵自发地组织起来,去老挝祭奠牺牲在那里的烈士。吉林延边籍烈士李保宇80多岁的母亲听说了这次行程,几经辗转联系到了老兵组委会,坚决要求参加团队,一定要去老挝看一看40多年前牺牲在那里的儿子。电话里,她泣不成声地叙述着40多年来无时不刻地想念儿子的心情,她不知道儿子长眠在哪里。她没有想到,儿子参军的那天就是母子俩诀别的日子。近50年来没有一个亲人去看过他,她放心不下儿子,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,她要在已经不多的有生之年,去看看离开她时还不到20岁的儿子。听到老妈妈的哭诉,电话这头的老兵们也是潸然泪下。组委会为难了,拒绝她显然不合情理,同意,又担心她的身体。幸好她的女儿和小儿子及时打来电话,承诺一路陪同,路途中出现任何问题不要老兵们承担责任,甚至愿意写下保证书。
老太太如愿来到老挝孟塞省的烈士陵园,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儿子坟前,如果儿子还活着也是一个甲子的老人了。岁月一晃就是近50年,第一次离儿子这么近,不过此时是妈妈在外头,儿子在里头。老妈妈扑在儿子的坟头老泪纵横,呼天喊地,捶胸顿足。一把鼻涕、一把泪地絮叨着近50年来的离别之苦、思儿之痛。时而,两手拍着坟头,仿佛是在轻轻地拍哄着熟睡的儿子。两个弟妹燃起一柱柱清香,烧起一簇簇钱纸,在坟头上撒一把家乡的泥土,坟前捧一捧老挝的泥土紧贴胸前,长跪不起,一声声地呼唤着“哥哥回家……”。近50个寒暑春秋,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梦寐以求,如今,生死相会于异国他乡,相聚于人间却未曾相见。
老妈妈是幸运的,有多少烈士的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便早早地离去,至死也不知道她们的儿子死在何方、葬在哪里。

在老挝纳莫县烈士陵园向烈士告别

福建晋江籍烈士王鸿胜和李保宇烈士一样,都是1971年5月14日那天,在美国轰炸机大轰炸时,牺牲在高炮阵地上的24位烈士之一。战斗中,他们击落两架美国F104战机,保住了南乌江大桥。
王鸿胜的妹妹在8位同乡战友的陪伴下也来了。他们的妈妈没有等到这一天,于一年前去世了。妹妹带着父母的遗言和家人的嘱托来到老挝。她一跨入老挝的国土,就从行囊中取出哥哥年轻英俊的遗像,紧紧地依偎在怀里。车窗外,看着哥哥曾经战斗过的异国原始森林,一路上泪水涟涟。近50年来对哥哥的思念,在心中无数次地、无声地呼唤着哥哥。今天,她突然情不自禁地、大声地呼喊起来,“哥哥,妹妹来看你了……。”那凄厉的喊声穿透了浓密的原始森林,竟没有一丝丝的回声,在层峦叠嶂的山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那悲恸欲绝的容颜,令同车的老兵们不忍侧目相视。老挝的山水旧貌新颜,可是,哥哥的音容笑貌今日何在?
她怀抱着抱憾而终的父母的遗像,在哥哥的坟前长跪哭泣。脸紧紧地贴着冰冷的墓石,与碑相拥,泪湿碑前,喃喃细语,尽情地向哥哥倾诉着无尽的思念之情,交待着父母的嘱托。不知道在奈何桥上苦苦徘徊,等待了40年的王鸿胜遇到了妈妈没有?他看到了长跪坟前,痛不欲生的妹妹了吗?听到了妈妈的嘱咐吗......?
老兵们也是泪如雨下、泣不成声,为长眠在老挝的战友,也为他们所有不曾相见的母亲痛彻心扉。苍天有眼啊!一直晴好的天气,突然间狂风大作,乌云遮天蔽日,携裹着暴雨倾盆而至。天上、人间共同地为他们而哭泣,也为天下所有的母亲而祈祷。
母亲的鲜血、乳汁、汗水和泪水铸就了军人的魂魄,用广袤大地般的情怀支撑着军人的脊梁。妈妈,才是当之无愧的、真正的英雄。


到老挝换装巴特寮军服的陈云豹

在老挝使用的货币军用代金券
(图片由战友陈永新、陈云豹提供)
2021年12月12日上传福春工作室